蓦然回首,母亲的爱,竟是如此的细腻,有力,持久。
有时,楼上米瓮里大米减少的速度让父亲困惑不已:怎么吃得这么快?
父亲哪里知道,母亲和三姐早已合谋,到远处湖田出工的时候,为了避免饥饿的袭击,她们通常会用三两杯白米去交换货郎担中的烧饼、麻花、油条等食品。
母亲的心究竟细到什么程度?
进餐时,每每不小心夹到自己不爱吃的白菜杆儿,或是不敢吃的辣椒,总是瞅准机会,偷偷地往桌子底下一丢。
从母亲数次发觉后的不予理睬中,极易推知这样的结论:这个动作只需瞒过严厉的父亲。事实上,餐后必打扫地面卫生的母亲是不可能不知情的。可是,一个孩童的自尊,除了母亲,还有谁会在意呢?母亲觉得,儿子的面子,她有维护的必要,对儿子的行为不置一词,便成了最好的选择。
每次放学回家,母亲便会找来一条柔软的干毛巾,擦掉额头和背部的湿汗;入睡,棉袄翻过来放在窗前的椅背上,鞋子搁到窗台上,经过一晚的风吹,第二天穿起来干爽舒适。
大冷天,每次上床前,一定会预先暖好被子;睡时,不断地帮我压好两肩及双脚处翘起的被褥;晨起,穿在里面的衣服,也一定是热热的,因为母亲已经提前在灶膛前烘烤过了。袜子呢?在没有生火的情况下,母亲也有办法,先把内层翻出来,放进自己贴肉的内衣处,一直到焐热后再翻过来,然后塞进床上的被窝中备穿。
大热天,洗澡后要穿的衣服一定会被搁在澡盆旁候着;睡觉前蚊帐也一定是已经放下来扎紧在床上的棉絮下面。在夜幕降临前,床帐里的蚊子,都提前被母亲用大蒲扇给驱逐了。
每到过年,母亲一定会请来裁缝,为大家定制一身新衣。当然,父母亲自己除外。
念中学时,每周返校,母亲也总是偷偷地塞给我一些额外的钱,“在学校,千万别饿着自己!”
犹记得,孩提时,三四公里远的隔壁大队放露天电影,哥姐嫌我人小走不快,不让同行。在匆匆料理完家事后,母亲总是愿意不辞辛苦地陪伴前去。
那劈山救母的二郎神,到底是从哪儿弄来的开山巨斧?母亲,并没有给我一个正确的回答。
父亲故去后,没有了顶梁柱的母亲非但没有垮掉,反而变得更加强大。
因常年累月洗冷水而落下的慢性支气管炎,竟莫名其妙地消失了。
家中的两三亩田地,在哥姐们的帮助下,继续耕种着。
甚至,在农闲时,母亲还会同村里人一道,去数里外的畈地上,帮主人采摘棉花,栽种油菜,挖挖花生,以此换取些微劳动报酬。
虽年近六十,干活细致,又不偷奸耍猾,速度并不快的母亲,依然受到了东家的欢迎。
每次寒暑假返家,总是发现楼上多了一副挑子,或者馒头,或者麻花,或者烧饼。
我为母亲的所作所为心酸沉痛不已。
这些货物,是母亲徒步七八里路,远去童司牌,在那儿批发了之后,再肩挑回来的。
六七十斤重的货担,母亲要穿过多少条乡间小路,才能把这些吃食,卖给散落在远近不同的村子里的需求者?
更为关键的是,母亲一直从事农业生产,怎么就为了供我求学,竟干起了自己从未做过的小生意呢?
最让我无法面对的事情,——母亲错误地接受了隔壁同族奶奶、叔伯婶娘的影响,每次都会跟医院,进行有偿献血。
“她们的血,医院不怎么想要,价格也低好多。因为抽血前,她们都喝了很多的盐水,血要稀很多。我没有喝,抽出来的血,颜色红红的。医生内行得很,骗不了。”
母亲没有丝毫的生理知识,讲出来的话让我既震惊又痛苦。
同族奶奶、叔伯婶娘肥胖,她们不定期献血,是因为血液粘稠会导致脑供血不足,献血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减缓头晕症状。可母亲,身材瘦弱,又偏素食,并无献血的必要。
母亲在我发觉情况并不断追究质问时,信誓旦旦,承诺再也不去了。可事实上,依然背着我去了三四回。
细腻的母亲是否知道,以这样的方式挣回来的钱,要强的儿子,怎么可能忍得下狠心去花掉?
毕业参加工作后,我约法三章,严格规定了母亲的劳动范围。
每隔半个月,我都会回去一次,看看母亲是否遵守规定。
捎两三斤猪肉,虽然母亲并不肯吃多少,可是,母亲为家人烹制肉菜和我们尽情享用时的快乐,怎么能省去呢?
每隔半个月,母亲也会往我的单位跑一次,每次都没有空手,不是新鲜的鸡蛋蔬菜,便是新鲜的大米。
其时,母亲并无农田,大米是怎么来的呢?
原来,母亲在农人收割完毕,冒着秋日的寒凉,在一片又一片的湖田中,赤着脚,弓着腰,一根根地拾起被主人遗弃的稻穗,捆成捆,背回家,捋下稻粒,用晒垫子晒干,用簸箕扬去灰尘,在攒够数量后,再以袋装的方式,分批分次扛到村上加工而成。





 当前时间:
当前时间: 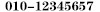 E-Mail:
E-Mail: